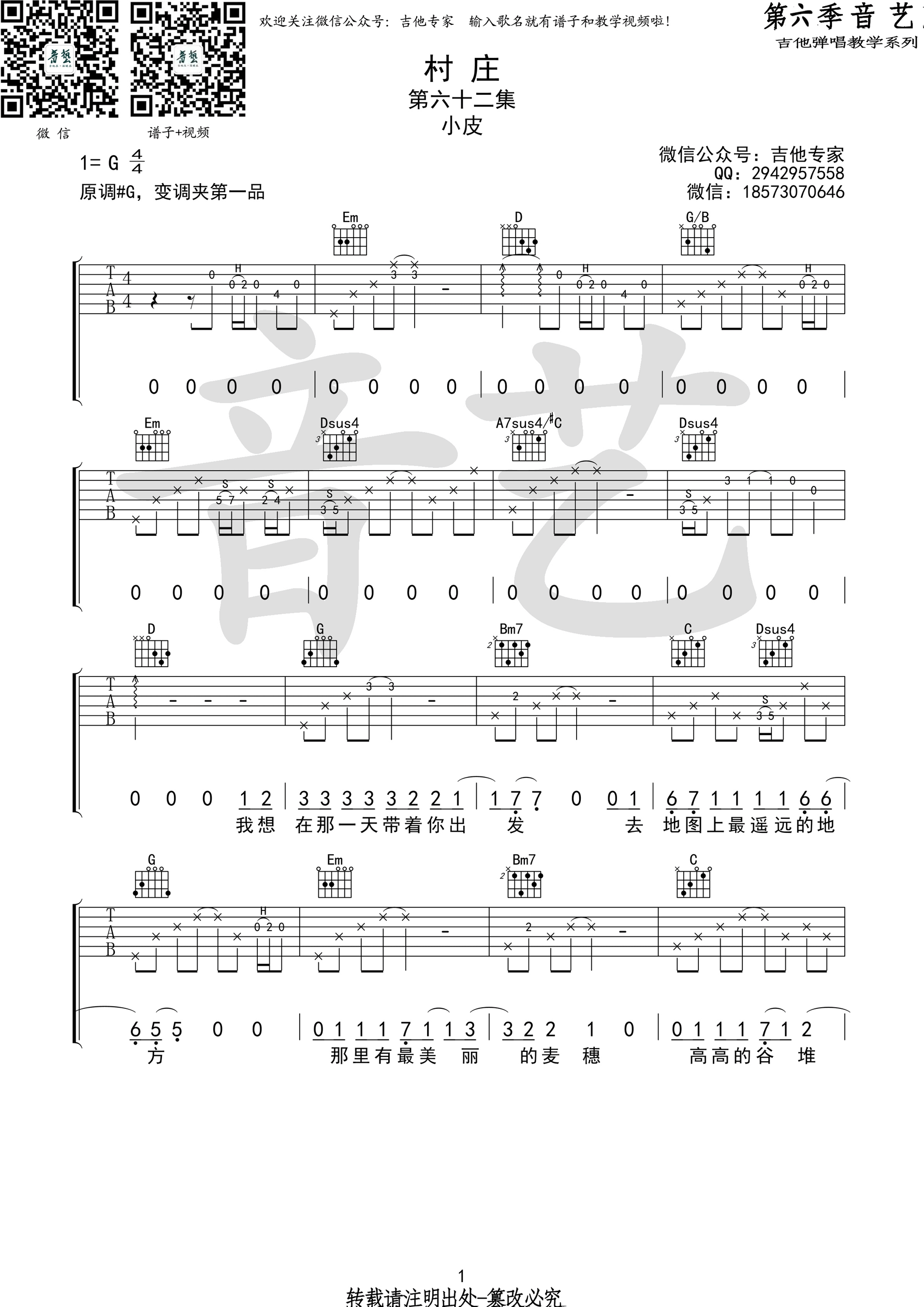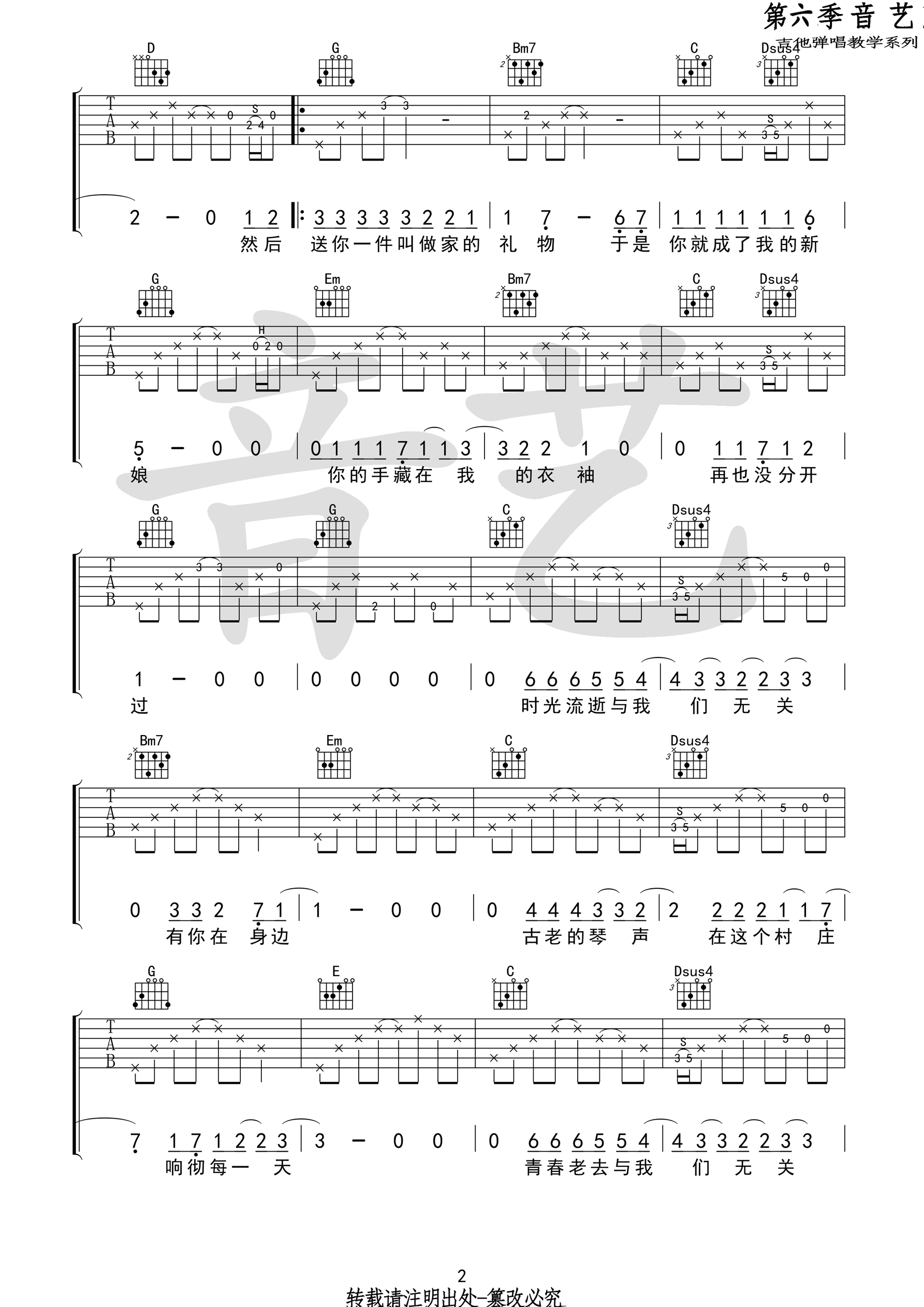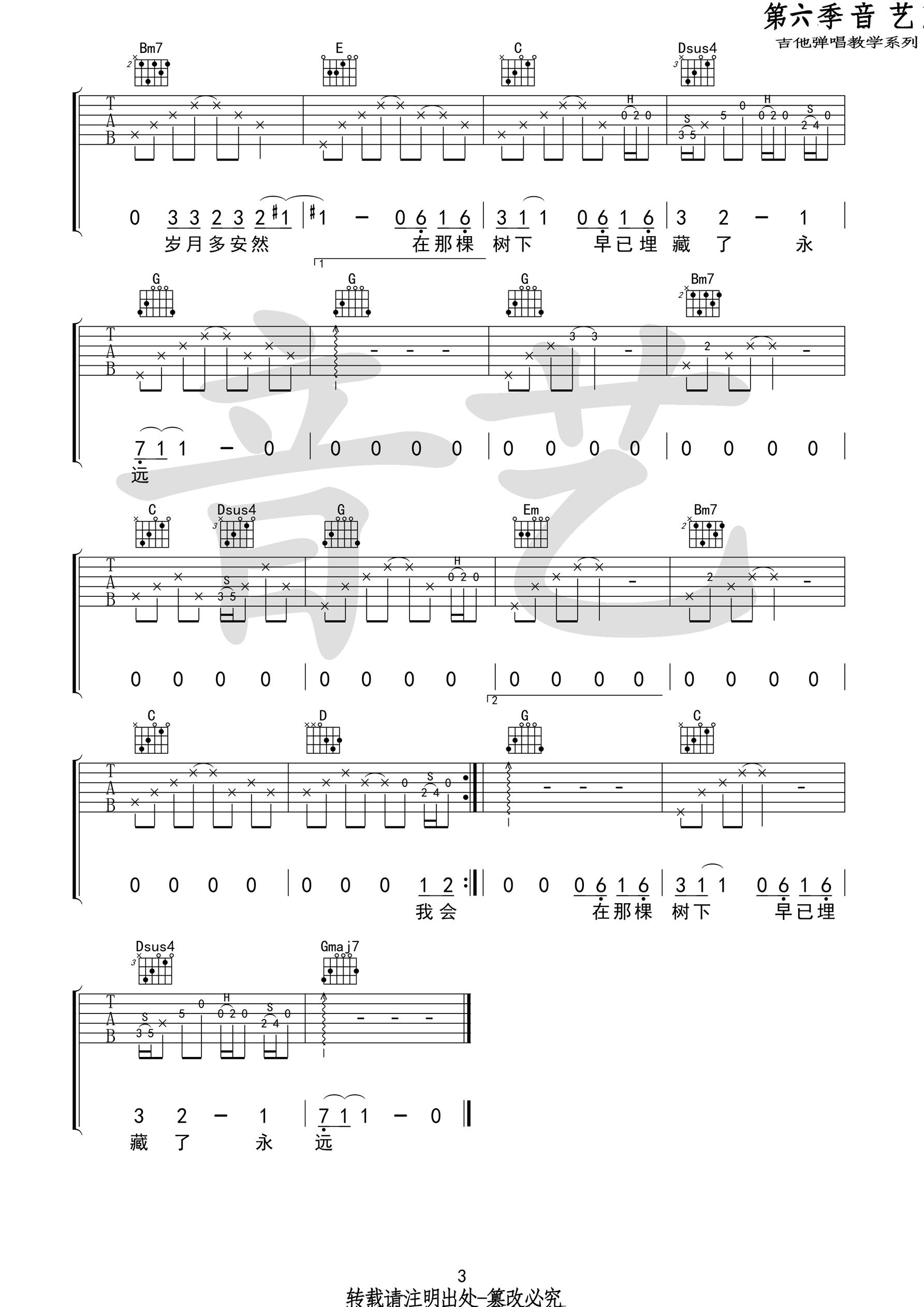《村庄》以质朴的意象勾勒出农耕文明的精神原乡,稻穗低垂的姿态与炊烟弯曲的线条构成血脉深处的图腾。土地在歌词中既是具象的生存根基,又是隐喻的文化母体,犁铧翻开的黑色浪花里沉淀着二十四个节气的古老智慧。井台边的陶罐盛满月光,这种静物式的书写暗示着循环往复的农耕时间美学,而晒谷场上的麻雀群像则突然打破凝滞,赋予画面生命的颤动。迁徙的候鸟作为现代性符号出现,其飞行轨迹与传统村落形成张力关系,屋檐下悬垂的辣椒串像凝固的火焰,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界处燃烧。方言在童谣中逐渐褪色,碾米机的轰鸣取代石臼的节奏,这些细节暴露出文化基因的嬗变疼痛。老槐树年轮里藏着的族谱故事,与智能手机蓝光映照的脸庞形成蒙太奇对照,祠堂门楣上"耕读传家"的匾额正在电子屏广告的霓虹中模糊。歌词最终将村庄升华为精神脐带的意象,那些消失的蓑衣斗笠在数字云端重构为新的文化染色体,而土地深处的根脉始终以沉默的方言,讲述着关于生存、消逝与重生的永恒寓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