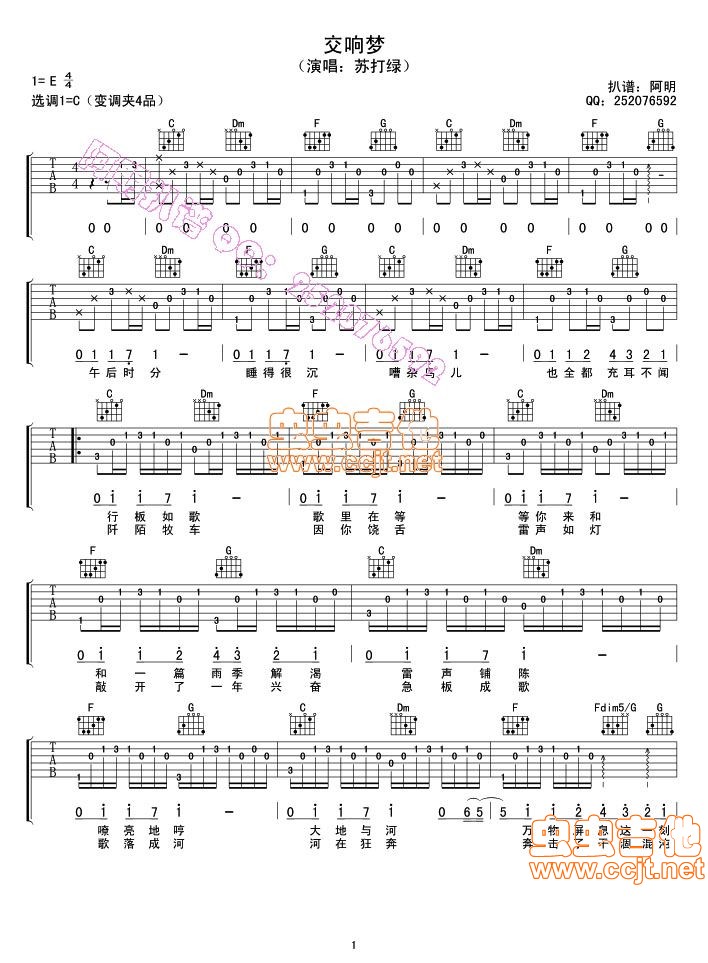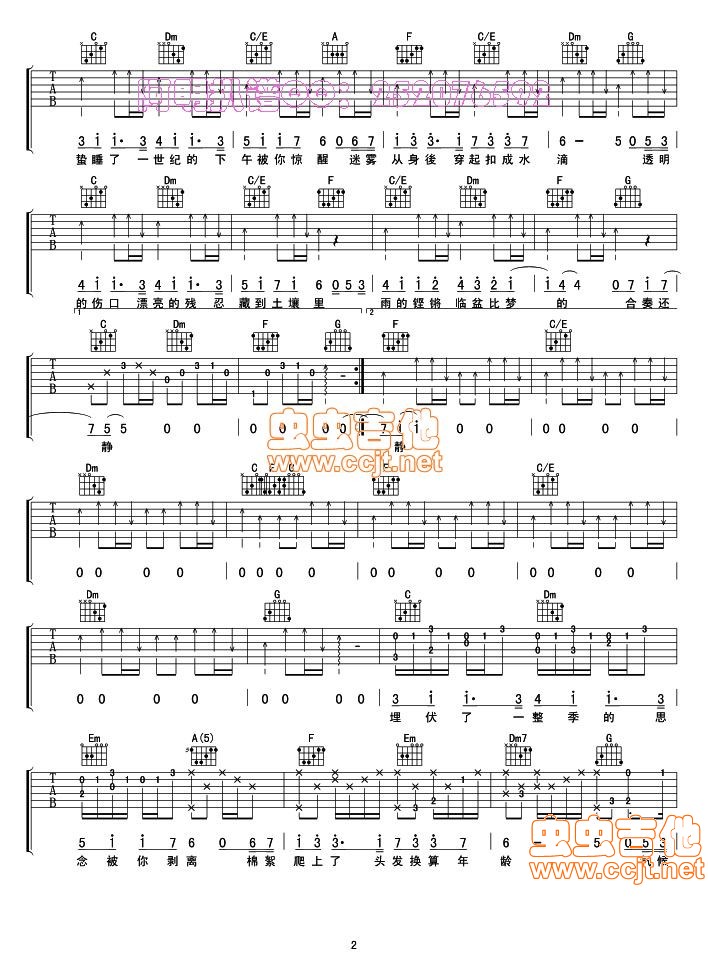《交响梦》以宏大的交响乐为意象载体,通过流动的旋律性语言构建出生命与艺术共振的深层隐喻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乐器拟声词不仅是听觉摹写,更暗喻着个体在命运洪流中寻找和声的生存姿态,铜管组象征激昂的生命宣言,弦乐组化作绵长的情感脉络,打击乐则成为时间流逝的具象化刻度。潜文本中涌动着艺术创作与存在困境的双重变奏,排练厅里永不完美的合奏对应着现实世界的残缺美,总谱上修改的墨迹揭示着持续自我修正的精神历程。城市霓虹与古典乐器的光影交错间,现代性焦虑与永恒艺术追求形成复调对话,而指挥家悬而未落的手势则凝固成存在主义式的抉择瞬间。当休止符被赋予与音符同等重量时,歌词完成了对沉默价值的重新发现——那些未被演奏的空白恰是艺术最深邃的留白。最终在渐强音中升腾的并非廉价的理想主义,而是认清生活本质后仍选择以艺术秩序对抗混沌的悲壮勇气,每个音符都成为刺穿虚无的微小光芒。